北宋如此,南宋更加变本加厉,南宋的武将,以认文官干爹为荣。在宋朝,官员之间的鄙视链大概就是:平民科举出身的看不上贵族科举出身的;贵族科举出身的看不上贵族恩荫做官的;贵族恩荫做官的看不上只袭爵啥都不干的;只袭爵啥都不干的看不上做武将的;剩下做武将的就和基层士兵报团取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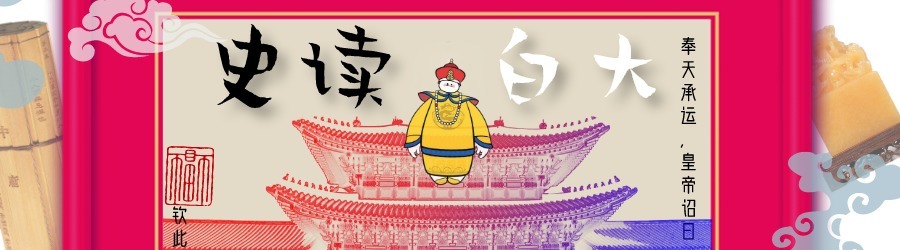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盛家老太太的一番话被大家狂赞,在儿女婚姻上,她说太高了不好,太低了也不好,两家最好家境相当,平交。

高攀的,女方在夫家底气不足;低嫁的,日子长了难免心生怨怼。
但是《知否》中,众人眼中所谓的几个高嫁,都是公候之家。第一,齐衡小公爷,父亲是国公,母亲是养在皇后膝下的郡主,家世可谓显赫;第二,梁家嫡六子梁晗,伯爵府,世袭爵位;第三,顾家嫡二子顾廷烨,侯爵府,世袭爵位。尤其是新皇继位,顾廷烨在皇帝登基之路上立下大功,成为当朝炙手可热的新贵。
这些身份,看似都不是一个五品官的小庶女能高攀上的。剧中其他人的意思也是,痴心妄想,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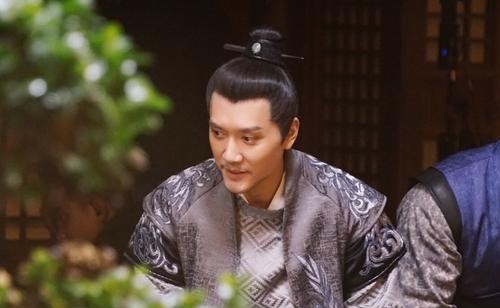
大家都知道宋朝重文抑武,其实在宋朝成立初期,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主要目的是让文武平衡,相互制衡。以免武将手中有兵权,起了造反的心思。但是这种平衡在一朝一朝中打破了,到宋仁宗时期,文官的地位是你想象不到的高,而武官的地位也是你想象不到的低。
宋仁宗时期,范仲淹、韩琦、苏轼、富弼、王安石等等才俊层出,他们的名气直到现在,一点不比当时差。但是提起宋朝的武将,最出名的还是被秦桧迫害的岳飞,而宋仁宗时期,只有一个狄青有点名气。
当时,在外带兵打仗的都是文官做主帅,文官才有调兵的最终决定权,而武将只能听文官的。有时候这些文官不能决定的,就要将情况快马发到朝堂上,让那个皇帝审批拿主意,群臣讨论,等再把解决方法送回去了,往往已经错过攻打的最好的机会了。

名将狄青,最高也就做到了枢密院副使,因为宋朝的正职只能由文官担任,武将最高只能做到副职。而且狄青驻扎在外,无命令不得回京,就算是十万火急的事情,也不能擅自回京。

那个时候,宋仁宗病重,于是朝臣就直接做主把狄青贬谪了。为什么贬谪?对,狄青也想知道,所以狄青亲自问,得到的答案仅仅是:我们怀疑你要造反了,所以要提前下手。
连直接证据都没有,就可以贬谪一位将军。
康姨妈的母亲一看这个受不了了,我闺女没了,我要讨公道,直接告御状去了。当时皇帝是恭恭敬敬把老妇人请到朝堂上的,而且因为旁边朝臣的添油加醋,直接把顾廷烨下狱,准备流放了。
顾廷烨,从龙之功,侯爵,大将军,因为杀了这么一个女人,竟被下狱流放。而明兰也告御状的时候,在宫外敲了一整天的登闻鼓,也没有人让她面见天子。

虽然后来我们知道了这都是皇帝和顾廷烨联手做的一场戏,但是这是真实反映了宋朝文武官之间的地位情况的。
宋朝不杀文官,但是可以杀武官。虽然宋朝也有文武双全的文官,能指挥的了打仗,但是也只有范仲淹这样的人才,而整个大宋的文人里,有几个是像范仲淹一样。更多的是把武将的功劳揽在自己身上,一边继续贬低武官,一边继续吹捧文官。
而武官的屈辱不仅如此,在宋朝,每一个基层出生的小士兵,都要在脸上刻字,类似于黥刑。在脸上刻字,这几乎是屈辱了,当个兵还得忍受这种屈辱。而且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干什么都不能当兵,就算是做个商人做点小买卖都不能当兵,否则就会被人看不起。

在剧中,顾廷烨一回京,很多人争着要把女儿嫁给他,当盛紘和王大娘子得知顾廷烨要娶他们家女儿时,也是惊讶出表情包。然后王大娘子就兴冲冲向如兰表示这是天大的好事,这门第比墨兰嫁的伯爵府还高。
讲道理,这两家在文官眼里都是差不多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家里带的兵比较多,一个家里带的兵比较少。

再说盛家,盛家祖上是商人,到盛紘的父亲科举出身,还娶了勇毅候独女,再到盛紘,也是科举出身,才敢去王家提亲。
而盛家的二房经商,家里有钱,据原著的描述,盛家二房每年往盛紘这里送钱都是一车一车的送的。他们第一次见到乖巧可爱的明兰,除了每个姐妹都有的礼物,随手就给了一荷包金子。

即便是面对权贵,比如小公爷家和梁家,梁家还不如顾廷烨,世袭的爵位,没有什么实质的官职,手里仅仅有几个兵,巡视京都。而小公爷家,国公,郡主,在剧中配公主都是足够的。事实上这样的家世,越是清贵文官越不会将女儿嫁进去。
什么叫清贵,清,就是觉得自己但凡跟权贵沾上点关系就不干净了;贵,就是越在朝堂上不结党不营私,自己一个人,就越显得贵重。在这种思想下,北宋的文人是不会想要跟权贵沾上一点关系的。

宋朝的确是一个经济高度繁华,文化高度繁华的朝代,这种繁华,就是以打压武将换来的。每个朝代都有每个朝代的治国方法,宋朝牺牲了武将的利益,让人们的视线都转移到经济生产和文化创作上来,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经典传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