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已进入新阶段,当前的焦点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中美之间的关税。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中美关税的具体方案即将敲定。这就涉及到中美关税最终会如何确定?影响中美关税制定的关键因素有哪些?而这一关税政策落地后,又会对中国乃至美国的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各方关注的重要议题。
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在当前中美关系的背景下,中美关税问题可能出现哪几种结果?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我们将展开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首先,分析当前中美关税的基本现状;其次,中美关税可能面临的几种方向性选择;再次,中美关税问题的主要矛盾点;第四,未来中美关税战对两国经济的潜在影响;第五,结论与建议。

一、目前中美关税的基本情况
谈到中美关税,目前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明确。
首先,2025年5月12日,中美双方宣布暂时按照10%的关税执行,而这一关税的依据是建立在4月2日美国宣布的34%关税基础上的。因此,剩余的24%被暂时搁置,等待未来正式关税方案的推出。
此外,此前在2月1日,美国对中国实施了芬太尼相关关税,3月1日又追加了另一部分关税,两者合计约20%,三者合计30%。如果再加上拜登时代和特朗普时代遗留的25%关税,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整体关税水平约为55%。而中国对美国的关税则维持在30%左右,这主要是历史原因形成的。
在5月12日中美于日内瓦达成关税共识之前,双方曾经历了一轮激烈的关税博弈:4月2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34%关税。4月9日,中国采取对等措施,也将关税上调至34%。随后,美国立即将关税提高至84%(即增加50%)。中国再次对等回应,将关税调整至84%,美国则进一步加码至125%。4月中旬,中美双方的关税已飙升至125%,中国对等提纲关税,形成所谓的"关税战"。如此高的关税使得中美贸易几乎陷入停滞--货物运输中断,贸易结算暂停。而美国甚至对部分商品进一步加征245%的关税。这是截止5月12日中美在日内瓦达成关税协议时的基本情况。
5月12日关税协议达成。经过三天的谈判,美国将关税降至10%,并将剩余的24%推迟至后续谈判决定(原定于8月12日,即90天后)。同时,此前所有增加的关税(84%、125%、245%)全部取消。不过,这一协议附带条件:中国恢复对美国稀土供应(关键因素); 中国采购美国波音飞机;美国则解除了对华发动机、乙烷的出口限制,并放开了H20芯片的供应。
此后,中美在6月9日于伦敦再次接触,主要讨论稀土供应问题,并达成相关协议。随后,7月30日,双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新一轮关税谈判,唯一达成的共识是将24%的搁置关税再延长90天(原定8月12日重新制定关税,但美国要求延期以便进一步谈判)。
这是截至目前,中美关税的基本情况和最新进展。
二、中美关税最终会如何收场?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美之间的关税问题几乎每个月都在调整--2月1日加征关税,3月1日再加关税,4月2日又一轮加税,而到了7月底,双方再次谈判关税延展问题。现在,关税问题已经被纳入一揽子谈判要求之中。
比如,在这次斯德哥尔摩谈判中,美国提出了一项关键条件:中国不能购买俄罗斯和伊朗的石油。我们简单算一笔账:中国每年从俄罗斯进口约1亿吨石油,而全国石油总消耗量约为7.5亿吨。此外,中国还从伊朗进口约2000万吨,从沙特进口约1亿吨,再加上其他来源,全年进口总量约为5.5亿吨,而国内产量2亿吨。也就是说,中国石油供应高度依赖进口。具体来看,中国每年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花费约为600亿美元(1亿吨),而总进口石油的支出则高达3000多亿美元。石油进口是一笔巨大开支,但中国最大的外贸支出其实是芯片。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在斯德哥尔摩谈判中强硬要求中国停止进口俄罗斯和伊朗石油,尤其是俄罗斯石油。然而,中国的立场十分明确:外贸政策属于国家主权范畴,因此拒绝了美国的要求。
作为回应,美国在7月31日由贸易代表贝森特(在会见特朗普后)召开记者会,提出新的关税方案:如果中国不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美国将把对华关税提高到100%。中国的态度依然坚决,表示中国有权自主决定贸易政策,并愿意承受100%的关税。

因此,到7月底,美国的立场已经明确:要么中国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要么关税恢复到100%。而近期美国的另一表态显示,他们可能要求关税回到4月初的水平,即34%(也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24%)。如果这样,加上此前2月、3月的20%关税,以及拜登时代的25%关税,美国对华总关税可能达到79%。这将导致中美贸易大幅萎缩,甚至可能使全球出口减少40%以上,影响非常大。
这样一来,摆在面前的选择就两个:第一, 中国继续进口俄罗斯石油,美国将关税提高到100%(重回4月的关税战状态);第二, 美国暂时维持24%的搁置关税。目前的关键在于,未来三个月的中美谈判将决定最终走向。谈判的底线是34%,上限按100%。这就是当前中美关税博弈的基本态势。
以上是我们对中美关税未来可能走向的分析。
三、影响中美关税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中美双方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关税谈判小组。美方代表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中方则由副总理何立峰和谈判代表李成钢领衔。中美在关税谈判方面涉及到几个议题。
首先是稀土问题。美国希望中国放开稀土供应,但中国坚持可以供应,但必须实施管控,特别是限制稀土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这一立场是美国无法接受的。这成为双方谈判的第一个重要分歧点。
其次是能源贸易问题。美国强硬要求中国停止进口俄罗斯和伊朗石油,而中国则坚持自主决定能源进口政策。这一争议直接引发了新的关税威胁,成为谈判桌上的第二个关键议题。
第三个争议焦点Tiktok的问题。美国是希望中国把Tiktok卖掉,中国则表示宁可关掉也不能卖。
第四个问题涉及到发动机和芯片专家徐泽伟以及富国银行毛晨月相关事宜等。这是中美之间关税的谈判背景问题。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能看得到中美的关税是交织在一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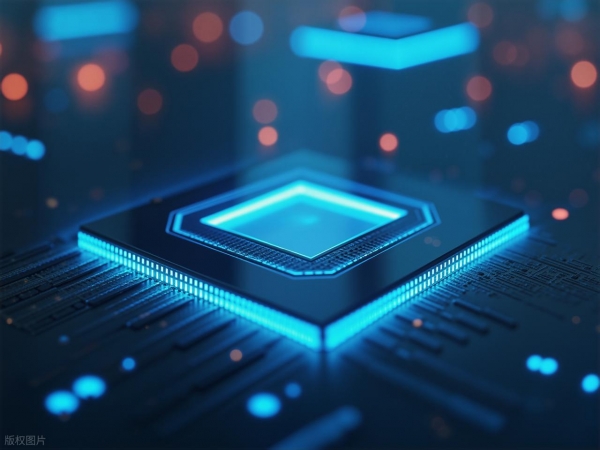
除此之外,美国还在其他领域施加压力:禁止中国采购高端光刻机,并要求其贸易伙伴国在对华贸易中实施"服从性测试"。例如,美国与越南达成的协议规定,越南出口美国商品适用20%关税,但同时要求越南采购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特别条款规定,经越南转口的中国商品将适用40%关税,为此越南专门对中国产品加征27%关税。各国在美国要求下普遍对中国产品额外征收20-30%关税,显示出美国试图全面遏制中国贸易的意图。
面对美国的关税施压,中国也采取了针对性反制措施。在芯片方面,中国加速推进国产化替代;在贸易封锁方面,中国以稀土出口管控作为反制手段,未来还可能运用石墨等关键资源。这些反制措施已显现出显著效果。同时,中国持续加强先进武器装备研发,在太平洋等重点区域的军事存在也对美国形成有效威慑,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中美关税博弈的天平。
四、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
中美关系目前呈现出多层面的复杂性,包括贸易关系、关税战、留学生问题等多个方面。虽然关税战是当前焦点,但从2025年上半年的贸易数据来看,中美贸易规模正在明显萎缩。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对美出口减少16%,5月份减少21%,6月份减少15%,整个第二季度总体下降15%-20%。按全年计算,中国对美出口约5400亿美元,美国对华出口约1600亿美元,原本38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可能缩减约1000亿美元。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在美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已从鼎盛时期的21%降至目前的14%以下,未来可能进一步降至10%以下。
然而,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虽然中国对美出口达5400亿美元,但美国在华投资高达5000亿美元,这些美资企业在华年销售额约7000亿美元,其中约3000亿美元产品返销美国,为美国企业创造约500亿美元利润。这意味着中美完全"脱钩"难度比较大,涉及上万家企业、5000多亿美元投资。其次,中美在多领域存在国际合作,完全中断关系的可能性较小。当前态势更可能是"互有反制"的博弈状态。
美国这次对中国的策略是也是比较坚决的:对英国实行10%关税,对日本、欧盟、韩国15%关税,但都附加采购要求。例如英国需采购美国农产品,日本承诺5000亿美元投资(90%利润归美方),韩国需采购3500亿美元商品,欧盟则面临总计1.35万亿美元的要求(其中7000亿采购、6500亿投资)。越南等国家同样在20%关税基础上承诺2000亿美元采购。这种模式预示着,未来中美若达成协议,可能既要接受更高关税,又要增加对美国商品的采购。
市场反应印证了这种紧张态势。7月31日(8月前最后一个交易日),A股市场全线下跌,香港资本市场更是连续三日下挫。进入8月后,受贸易战升级、关税问题及复杂国际局势影响,资本市场预期并不乐观。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中美关税问题的深入分析,我们得出两个主要结论:
第一,当前中美在关税问题上的对抗态势明显强于合作意愿,而且中美的贸易总量在减少。
第二,美国在打关税战时是有顾忌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在稀土等关键资源领域的反制能力,使美方在制定政策时必须权衡得失。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意味着双方仍将保持谈判渠道,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未来中美关税水平很可能会维持在25%以上,同时双边贸易总额将进一步收缩,这将对我国下半年经济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面对这一形势,我国已采取多项应对措施:一方面通过重大基建项目拉动内需,包括雅鲁藏布江开发(投资约1.2万亿)和京莫铁路建设(投资约1.5万亿)等近3万亿规模的投资计划;另一方面,7月30日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严控新增债务,同时大力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为经济转型提供多元支撑。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两点建议:
首先,外贸企业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应对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冲击。既要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也要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其次,中国必须加速高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步伐。实践表明,我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突破越多,美国实施技术封锁的效果就越有限。
以上是我们对当前中美贸易关系下关税博弈态势的基本分析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