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想过,人类可能永远无法离开地球?
不是科技不够,而是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监狱"。

人类向来是自大的动物,自以为是万物之灵,是宇宙的中心,是造化的宠儿。然而倘若我们肯稍稍抬头,向那无垠的夜空投去一瞥,便不难发觉:我们不过是囚禁在一粒微尘上的囚徒罢了。

地球诚然是广大的,然而在宇宙的尺度上,不过是一粒悬浮在阳光中的微尘。旅行者1号在六十亿公里外拍摄的"暗淡蓝点",已经将我们的处境说的明明白白,我们在这蓝色牢笼中生,在这蓝色牢笼中死,自以为翱翔,实则不过是在牢笼中扑腾。大气层便是这囚笼的栅栏,将我们与浩瀚的宇宙隔开,我们向外张望,却难以触及。

人类的历史,便是一部越狱史。起初用神话想象着飞天,嫦娥奔月,伊卡洛斯振翅,都是囚徒对自由的幻想。后来有了科学,囚徒们开始丈量囚笼的尺寸,伽利略的望远镜,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不是囚徒们在摸索牢房的构造。而今,我们终于能将探测器送出牢笼,却发现自己依然困在原地。火星太远,金星太热,木星的气旋能将人撕碎。太阳系的其他地方,竟没有一处能容这具脆弱的人类躯体。

这囚笼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同时也是庇护所。大气层阻挡了致命的辐射磁场,偏转了太阳风,恰到好处的距离使我们免于被烤焦或冻结。这囚笼造得如此精巧,以至于我们一旦离开它,便会立即毙命。宇航员在太空中的种种不适,不过身体在抗议:回到牢笼里去,那里是你该待的地方!

现代人尤其感到这囚禁之苦,信息时代将宇宙的浩瀚无情的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火星的照片,听到关于星外行星的新闻,却连隔壁的城市都懒得去,知道的越多,越感到被困的憋闷。网络给了我们一种需虚假的自由感,仿佛点击鼠标就能遨游太空,实则我们的肉体依然困在这具皮囊中,困在这颗星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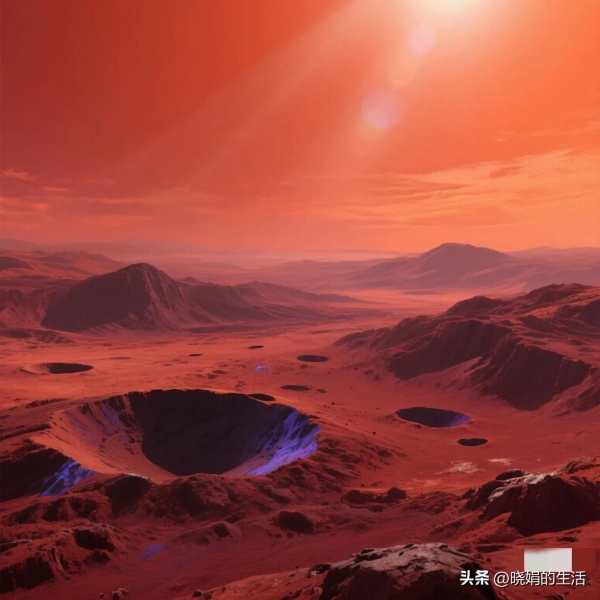
然而,或许正是这种囚禁,造就了人类的一切,牢笼逼出了智慧,因为不能飞,所以发明了飞机;因为不能长生,所以创造了艺术;因为困在地上,所以抬头仰望星空。所有的文明,所有的哲学,所有的科学,都源于对这囚禁状态的反抗。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漂泊十年只为回家,这何尝不是人类处境的隐喻?我们永远在寻找归宿,却永远在路上。

那些最敏感的心灵最先感到这囚笼的压迫。屈原问天,但丁游历三界,梵高画旋转的星空,都是囚徒们的呻吟,而普通人则用更朴实的方式对抗囚禁:生儿育女,建造房屋,种植庄稼,在有限的时空中创造无限的意义。每一首情诗,每一幅画,每一个微笑,都是向宇宙宣告,即使被囚禁,我们依然可以活得更自由的人。

也许有一天,人类真能大规模离开地球。但我们带走的,依然是地球塑造的身体和心灵。我们将永远是地球的孩子,无论走到多远,囚笼已经烙印在我们的基因里,成为我们存在的一部分。

夜深人静时,我常想:或许真正的自由不在于逃脱囚笼,而在于认识并接受它,然后在其中活出人的尊严。就像普罗米修斯,被锁在高加索的悬崖上,却依然保有反抗的意志,那才是人类最动人的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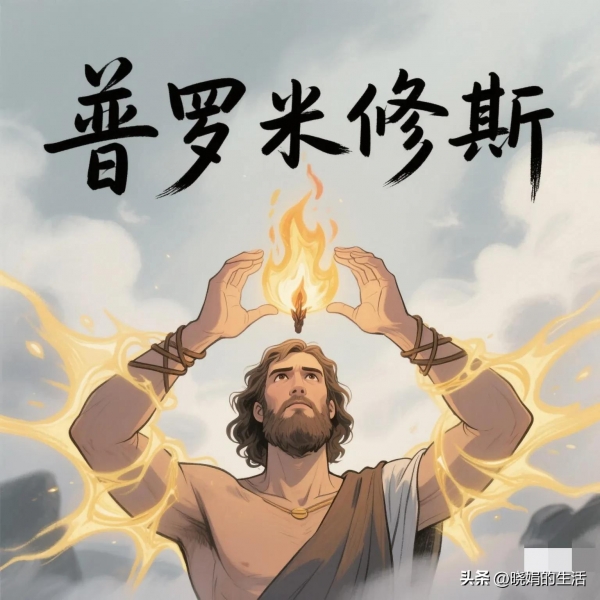
我们是被囚禁的星尘,却也是会思考的星尘,在这浩瀚的宇宙的一粒微尘上,我们爱过,恨过,创造过,毁灭过,这或许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