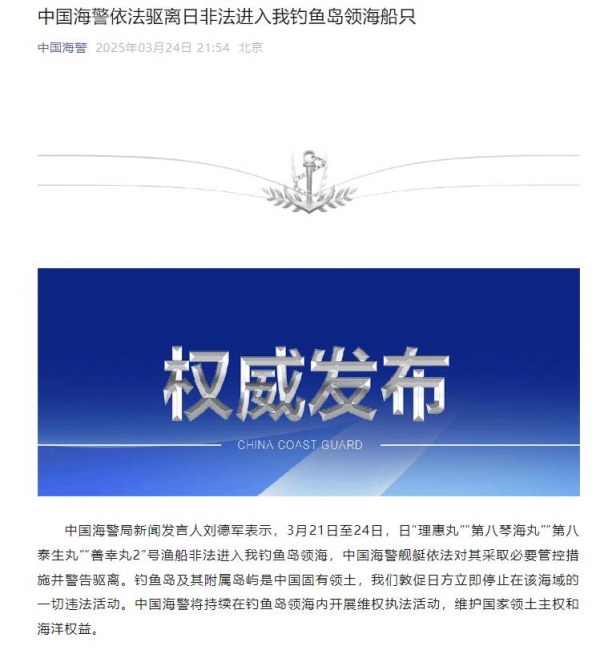3月2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日本东京同日本外相共同主持第六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丰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经济领域内涵,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经贸关系。
两天后,3月24日,日本自卫队"统合作战司令部"也在东京成立。日本共同社称,"统合作战司令部"由约240人组成,由59岁的南云宪一郎担任司令官,负责自卫队与美军间协调工作。共同社声称,成立"统合作战司令部"是为"防备大规模灾害和台湾突发事态",提升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有分析认为,该司令部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军事指挥体制的重大变革,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加速迈向"能战之国"的战略企图,对亚太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需要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日本这种"左手花束,右手倭刀"的矛盾姿态,恰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的经典论断,"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既穷兵黩武又恬淡宁静,既倨傲蛮横又彬彬有礼,既冥顽不化又温和善变,既效忠服从又自尊独立,既忠贞又叛变,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喜新。"
这种矛盾姿态并非偶然,是日本国民性和地缘政治宿命的必然产物,也是现实战略选择的必然。

一、岛国生存哲学的积淀
日本地处环太平地震带,每年有超过1500次有感地震,叠加海啸、火山、台风等灾害,形成"今日不知明日事"的危机感,以及"及时行乐"和"孤注一掷"的极端思想。
作为群岛之国,日本天生四面环海地理隔绝,形成了封闭自守的"神国意识",又因土地贫瘠,粮食自给率不足,食物长期匮乏,无时无刻渴望拥有大陆土地。而这种矛盾转化为--日本既渴望用外部先进文化、科技提高自身实力,又对外部威胁深刻焦虑,又渴望挑战外部力量,占领外部利益。
圣德太子的大化改新,以及明治维新后的全盘西化,让外部文化对日本内生精神世界任意撕裂重组,能留下的"本我精神"仅限最极端的一小部分,也最终形成了日本特有的"情境性道德",即道德体系由多个"世界"构成,每个情景对应不同的道德要求--行为规范一般更依赖外部评价,而非内在良知。
也就是说,一个日本人,可以有很多张"脸"。
这导致日本文化在站位上始终保持着灵活性和矛盾性并存。比如明治时代,武士可以为了"忠"参与倒幕运动,却可能因此背叛旧主背负道德谴责。
这种文化特质投射到现代国际关系中,就表现为日本可以同时与中国经济合作与安全对抗,或同时与美国经济对抗与安全合作。
二、地缘政治困境的现实投射
日本地处欧亚大陆东方边缘,太平洋西侧边缘,近现代一直处于"海权与陆权"博弈的夹缝之中,同时需要面对海洋霸权,比如美国、英国,和大陆强国,比如俄罗斯和中国的双重压力。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美国要求日本加强军事投入,提升军事实力,在中国特殊的两岸关系上加码,使之再平衡。这与二战后的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形成结构性矛盾。
日本政治精英也在矛盾,既希望摆脱"战后体制"实现国家正常化,又受制于国际社会舆论和历史认知,同时担忧被卷入大国对抗,成为战场炮灰。
而中日贸易连续多年突破3000亿美元,中国保持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即便特朗普要向日本汽车收关税,日本也无法彻底跳出"西方阵营",全力与中国合作发展经济……
这种矛盾,正是中日关系持续不稳的重要原因。
日本现在要亲中,还是反中?
这一点从日本人的文化认同上能够看出端倪,日本人始终在"东西方之间摇摆"。
3月24日,在会场里挂出"解衣"二字与中国谈合作"表忠心";
3月26日,成立统合作战司令部,渲染所谓"外部威胁",向美国"表忠心";
日本这种极端矛盾的姿态,其实是"日本式的中庸"。
解衣二字,是韩信对刘邦说的,"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在"经济"的世界里,日本亲中,在"安全"的语境下,日本反中。在其他人看来,日本是精神分裂,这却是日本的历史常态。这种矛盾性不会随着个别政策调整而消失,反而会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深化趋于复杂。
而中国,也在这么多年与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适应了日本的"神奇",谈是谈,打是打,经济是经济,安全是安全,项项分开,互不干扰,各自推进。
石破茂是日本的国家利益派,一切以日本利益出发,对中国来说,能谈就谈,不能谈就不谈……
归根到底,要看中国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